
作者:(智利)胡安·埃马尔
责编:侯明明
译者:梅清
ISBN:9787573510525
单价:49.0
出版年月:2025-04-01 00:00:00.0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学艺术
分类号: I784.45
语种:CHI
页数:175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评分:0.0
评分:0.0
(本馆/总:0/0人荐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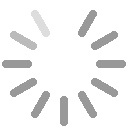
 目录
目录
前言
悬停日日
画作集
 导语
导语2025最疯感的拉美文学来了!可能是文学史头号“盲盒”作家!超前、抽象、古怪、幽默,他创作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当下日子看似滚滚向前,却随时可能拐入意料之外的方向。我受够了,咱们溜吧! 拉美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未来感十足,中文世界初次引进,既是小说又是画集,收录作家30幅全彩画作,与他同时代的南美作家喧嚣而孤独,而胡安·埃马尔安静又古怪。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给我们展现由不真实主管的生动世界,而这恰恰是永恒的一部分。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怎样才能抓住最普通的日子里,那些闪闪发光的记忆?或许可以用蹦极来类比。 在高处的悬崖边向下跳,体验急速坠落的感觉,随后在最/低点处被紧绷的弹力绳拽住。顿悟就发生在这个瞬间。 意识、潜意识、回忆、思维……脑海中的一切借着冲劲继续坠落,只有身体和感官悬在半空。在悬崖之下,一瞬间你看到所有的过往,昨日分散的碎片在眼前形成一个整体。紧接着绳子回弹,碎片迎面撞来,重新回到你的身体。 时间再次有序地展开,在日常的复杂状况中蜿蜒前进,片刻前的碰撞构成了人生中的新经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胡安·埃马尔(Juan Emar),1893—1964。 原名阿尔瓦罗·亚涅斯·比安奇,智利作家、艺术评论家、画家,拉美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 他是聂鲁达笔下的“我真有个朋友”,总穿一身囚服式的睡衣,低调又古怪。 他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数字,我就是一个数字。” 1893年生于智利一个富裕的家庭。 养过12条狗、24只母鸡。 13次往返欧洲,在官方活动、洗礼仪式和葬礼上打过289次哈欠。 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4部作品,又因评论界的冷遇整整26年没发表作品。 完成了一部4134页的小说,名为《门槛》。 在作品《悬停日》中创造了1座城市、831607个居民,每章节都以此结尾:“咱们溜吧!” 画过213幅画,画作签名会改成JeanEmar,谐音法语J'enaimarre,意为“我受够了”。 晚年靠亲人每个月给的50埃斯库多生活。 1964年被癌症夺去生命。
 前言
前言胡安·埃马尔的奥林匹克 运动会 青年时期,胡安·埃马尔 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他出 生在古希腊,一定将一生奉 献给艺术,沉浸到永恒而美 妙的孤独中,只有“烦人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打扰到 他。可见他一直幻想用一生 进行创作,不过他并不想成 为作家,或者说他并不想以 作家的方式行事,他只想专 心消遣,进行真正的探索, 无畏地接受玄妙之事与不确 定性。我们可以看到,《悬 停日日》中的叙述者就是如 此,毕生致力于艺术与内省 ,他在虚构的城市圣奥古斯 丁 - 德探戈市(这是属于埃 马尔的马孔多或者约克纳帕 塔法),“圣奥古斯丁 - 德 探戈”听起来与某座智利城 市格外相似:圣地亚哥闲逛 ,追寻一个“结论”或一束总 是从指缝中溜走的灵光。然 而他并非独自一人闲逛,他 有妻子相伴,身边还不断出 现其他人物,包括一位有多 热爱绿色就有多憎恨资产阶 级的画家,一个在所有故事 中充当主人公的大肚子男人 ,一个因自己的无私而被砍 头的可怜人,还有叙述者一 家人和乌拉圭领事。 胡安·埃马尔原名阿尔瓦 罗·亚涅斯·比安奇,朋友们 称他“皮洛”,在担任艺术评 论员的那几年他自称“让·埃 马尔”,与法语中的“J’en ai marre”相似,意为“我受够 了”。他不是与品达同时期 的,而是和安德烈·布勒东 同一代,他不出生在荷马的 祖国,而是出生在比森特· 维多夫罗和巴勃罗·聂鲁达 的故乡,这两位诗人是对头 ,却也都是胡安·埃马尔的 朋友,不过维多夫罗曾说“ 皮洛用脚写作”,这句不够 友善的话形同在朋友背后打 了一拳。然而,一九七〇年 ——胡安·埃马尔去世几年 后,聂鲁达曾写过一篇洋溢 着赞美之情的前言,前言的 开头是这样的:“我与胡安· 埃马尔是密友,可我从未了 解过他。他有众多朋友,但 他们又算不上他的朋友。” …… 一九七〇年,聂鲁达在 《十》的前言中草率地将埃 马尔与卡夫卡相提并论,引 发了对埃马尔的短暂吹捧, 这有点不公平,因为埃马尔 不是智利的卡夫卡,聂鲁达 也不是智利的惠特曼。我们 这一代智利读者很幸运,无 须在阅读埃马尔时将他与其 他人比较,但我也理解这种 冲动。我还记得在某节课上 ,我们拼命讨论埃马尔是否 比科塔萨尔好,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科塔萨尔是 公认的模范型超级作家,无 论唯美主义者、本质主义者 、活力论者还是投机主义者 都对他一样重视。我们没讨 论出结果,但我记得有人断 言,未来没人会读科塔萨尔 ,而埃马尔的作品会成为经 典的中心,所有人都或多或 少同意这个观点——这个人 不是老师,老师那天下午罕 见地谨慎,只是享受着无声 的胜利,因为他用了几个星 期就让我们成了胡安·埃马 尔的狂热读者。这是种轻率 的看法,当然还带点民族主 义色彩(或者说是反阿根廷 色彩——在我们国家,有时 候这二者是一回事),另外 这么比较也挺愚蠢的,有什 么必要将我们敬爱的两位作 家相提并论?但那是在九十 年代,一个可怕的时代,至 少我们还能在讨论时装作自 己是哈罗德·布鲁姆,常常 让讨论在爆发的笑声中结束 。 胡安·埃马尔领先于他的 时代,他无疑是为未来读者 而写作。假设这些读者就是 我们,是我们这些在他去世 后十五到二十年出生的人, 我们成长的地方与他所熟知 的智利大相径庭甚至更糟, 这种假设既显傲慢又令人激 动。可也许我们并非他的目 标读者。比如当我重读《门 槛》中的某些章节,或是《 悬停日日》炫目、混乱、美 妙的“量子”结局时,我觉得 胡安·埃马尔甚至不是为我 们而写。是的,我们可以阅 读他的作品,享受其中并自 认读懂了他,但在内心深处 我们知道,在尚未抵达的未 来,他的书将被更多读者更 好地阅读、欣赏和理解。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2021年于墨西哥城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书得科技有限公司()
浙B2-20110302号 馆员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