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编者:(英)亨利·哈迪
责编:顾舜若
译者:唐建清
ISBN:9787305287589
单价:68.0
出版年月:2025-08-01 00:00:00.0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社会科学
分类号: B512.59
语种:CHI
页数:2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评分:5.0
评分:5.0
(本馆/总:0/1人荐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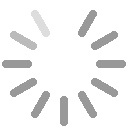
 目录
目录
序言
编者前言
作者说明
刺猬与狐狸
第二版附录
编者后记
索引
 导语
导语《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是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经典之作。本书以古希腊格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一件大事”为核心,将人分为两类,深入剖析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揭示人类内心的分裂性。 原著单行本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中译单行本首次面世,依据新修订版译出,新增伯林传记作者叶礼庭撰写的序言及丰富附录。伯林对比刺猬对统一真理的渴望与狐狸的现实感,指出我们内心兼具二者,需在接受知识不完整性与坚持确定性和真理间做出选择。 文章不仅关乎托尔斯泰,更关乎我们所有人,提出的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引人深思。只要人们寻求答案,这篇伟大文章就会持续流传。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一件大事”,这句古希腊格言出现在诗人阿基罗库斯的作品残篇中。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关于托尔斯泰与历史哲学的精辟作品的中心论点。尽管对这句格言的解释有很多种,但伯林用它来区分两种人:一种人着迷于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另一种人追寻统一的系统。这揭示了有助于解释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一个悖论:托尔斯泰是一只狐狸,却相信自己是一只刺猬。在本书中,伯林对托尔斯泰、历史认知和人类心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本书原著单行本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这是中译单行本初次面世,根据新修订的版本译出。修订版中新增了伯林的传记作者叶礼庭撰写的序言,该序言充分阐述了伯林文章的持久吸引力;附录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背景,包括相关评论和伯林的书信节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前言
前言这篇出色的文章最初是 在牛津大学发表的演讲, 1951年被一份鲜为人知的 斯拉夫研究期刊转载, 1953年被再次命名并被重 新发表。为什么这篇文章能 如此强劲而持久地流传下来 ,我们有必要加以阐明。与 《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一样 ,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区别也 被证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并被用于伯林此前从未想象 或计划过的领域。20世纪 30年代末,“刺猬与狐狸”最 初是教师休息室的一种室内 游戏——牛津大学的一位本 科生向他介绍了一个奇妙而 神秘的希腊语句子,以赛亚 就用它把他的朋友分为刺猬 与狐狸。后来,伯林将它变 成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著 名文章的结构性见解。“刺 猬与狐狸”现在已经进入文 化,作为对我们周围的人进 行分类的方式,以及思考关 于现实本身的两种基本定位 的方式。 狐狸不仅知道很多事情 。狐狸承认,他只是知道很 多事情,而现实的统一性肯 定是他无法把握的。狐狸的 重要特征是承认自己所知有 限。正如伯林所说:“我们 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更大 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自 己生活在这个整体中,并依 赖它,我们只有与它和平相 处才是明智的。” 刺猬不会与世界和平相 处。他不甘心。他不能接受 自己只知道很多事情。他试 图知道一件大事,坚持不懈 地要给现实一个统一的形态 。狐狸满足于所知道的,他 可能会过上快乐的生活。刺 猬不会安定下来,他的生活 可能不会快乐。 伯林认为,我们所有人 的内心都既有狐狸的一面, 也有刺猬的一面。这篇文章 是对人类分裂性的一种无与 伦比的描述。我们是分裂的 生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是接受我们知识的不完整性 ,还是坚持确定性和真理? 我们当中只有最坚定的人才 会拒绝满足于狐狸所知道的 ,而坚持刺猬所确定的。 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经 久不衰,因为它不仅是关于 托尔斯泰的,也是关于我们 所有人的。我们可以与我们 的“现实感”和解,接受现实 的本来面目,过我们现有的 生活;我们也可以渴望在表 象之下找到一种更基本、更 统一的真理,一种可以解惑 或提供慰藉的真理。 伯林将刺猬对统一真理 的渴望与狐狸的现实感进行 了对比。他坚信,狐狸的知 识也可以是扎实而清晰的。 我们并非在云雾中。我们可 以认知,我们可以学习,我 们可以做出道德判断。科学 知识是明确的。他所质疑的 是,科学或理性是否可以给 我们一种切入现实核心的最 终确定性。我们大多数人满 足于此。他写道,智慧不是 屈服于幻想,而是接受“我 们在其中行动的……不可改 变的媒介”“事物之间的永恒 关系”“人类生活的普遍结构 ”。我们有此认识,不是通 过科学或推理,而是通过对 现实的深刻理解。在生命的 最后几年,伯林本人获得了 这种宁静。这种宁静似乎源 于贯穿他现实感的接受与和 解。 少数人拒绝接受现实。 他们拒绝屈服,并寻求—— 无论通过艺术还是科学,数 学还是哲学——穿透狐狸所 知道的许多不同的事情,以 一个核心的确定性来解释一 切。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 一个人物,他是所有那些人 中最无法被动摇的刺猬。 刺猬的伟大之处在于拒 绝我们的局限性。其悲剧在 于最终无法与局限性和解。 托尔斯泰无情地蔑视一切关 于真理的教义,无论宗教的 还是世俗的,但他无法放弃 这样的信念:只要他能克服 自己的局限性,就能掌握某 种终极真理。“直到他生命 的最后一刻,托尔斯泰的现 实感都是毁灭性的,无法与 任何道德理想相容,他的智 慧将世界震碎,而这种道德 理想则是他从世界的碎片中 构建出来的。”最后,他成 了一个悲壮的人物——“一 个绝望的老人,无人相助, 就像刺瞎自己的俄狄浦斯, 在科洛诺斯(Colonus)徘 徊”——无法与自己人性中 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解。 这篇文章向任何阅读它 的人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 现实感”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是否甘于接受人类视野 的局限性?或者我们渴望得 到更多?如果得到更多,有 朝一日我们希望实现什么样 的确定性?因为这些都是人 类存在的永恒问题,所以, 只要人们继续寻求答案,这 篇伟大的文章就会流传下去 。
 后记
后记最近,尤恩·鲍伊对这个 残篇的可能含义进行了新的 解读。他认为这句话可能来 自一首诗,是阿基罗库斯和 他试图诱惑的女人之间的对 话。这句话可能是那个女人 说的,她说狐狸(阿基罗库 斯)也许有很多诱人的诡计 ,但她(刺猬)的武器库中 有一个决定性的手段,就是 蜷成一团,(至少从正面) 阻止他的进攻。希腊语中, “刺猬”一词也可能用来指女 性的生殖器,这将支持这种 解释。鲍伊的假设是基于两 份纸莎草残篇(分别于 1954年和1974年首次发表 ),其中一首抑扬格诗主要 是阿基罗库斯和他正在引诱 的女人之间的对话。在利用 狐狸与鹰的寓言(残篇172 —181)和狐狸与猿的寓言 (残篇185—187)进行创作 的诗歌中,阿基罗库斯显然 将自己认同为狐狸,这暗示 了他被描绘成狐狸而不是刺 猬。 葆拉·科雷亚在一篇文章 中介绍了鲍伊的假设,文章 明智地总结道:“对于今天 那些试图断章取义地阅读( 这一残篇)的人来说,它像 刺猬一样蜷缩起来,或许再 狡猾的人也不能在不用暴力 的情况下揭示它的某些含义 。”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书得科技有限公司()
浙B2-20110302号 馆员登录
